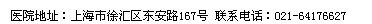您的当前位置:视网膜出血 > 网膜出血治疗 > 张明行医路上,那些事,那些人helli
张明行医路上,那些事,那些人helli
流过泪的眼睛会更明亮。
作为医生,一定要把自身的本领练好。没有足够的能力却要去担当,可能就会造成伤害。
他越这样说,我越觉得很对不起他。同时我也在反思,这种手术没有问题,出现术后并发症的情况,应该如何管理?
医患沟通是有医学专业知识的人和没有医学知识背景的人在沟通,尤其对于眼科这种专业性特别强的科室,一定要要尽量通过生活化和通俗的语言,帮助病人理解眼睛的结构和功能,理解疾病知识。
——《指尖上的光明》
//行医路上,那些事,那些人……//人的一生行色匆匆,总有一些人、一些事,因为种种原因,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。每位医生在行医生涯中,也总会因为某些原因,记住某些病人故事。下面这几个故事,就是我行医生涯中几个印象深刻的故事。
“我还要做另一只眼睛”
这是我会诊的一个病人,不到50岁的年纪,一只眼睛失明,另一只眼睛是晚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,视力只有0.1,眼底增殖得非常厉害,有很多新生血管,还有牵拉性视网膜脱离。
会诊之前,他的主治医生已经跟他讲明,病情很重,治疗价值不大,治疗后一旦出现并发症,这只眼睛也会失明,建议放弃治疗。
会诊时,看到病人这种情况,我也很犹豫。治,风险很高。病人来自农村,没什么文化,医院,也没有家属陪伴。他只关心一件事,做手术要花多少钱,花了钱是不是比现在看得更清楚?不治,随着糖尿病病情的进展,这只眼睛迟早会像另一只眼睛一样走向失明。
仔细评估病情后,我决定跟他沟通一下。我说:“如果放弃治疗,这只眼睛一定是走向‘死亡’,也就是失明。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来努力?我们拼一次,‘赌’赢了,这只眼睛可能还能看到光明。你还不到50岁,能看到光明,今后的生活就能不依赖家人照顾。”
但病人却一直在说,家里所有的积蓄都被他拿来看病了,花了钱就应该能看得到。
这个时候我也纠结了。我说的是应该考虑“赌”一次,不“赌”,一点机会也没有,“赌”,也许会有点机会。但病人反复就问一点,我花了钱是不是比现在好?他的主治医生也对我说,要做你做,我不做。
压力一下子全到我身上来了。
这天回去以后,我仔细思考了很长时间,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技术,我决定还是要去“赌”一下。就在第二天手术日把他加进去了。
手术做得很顺利,术中止血和膜处理得比较彻底,术毕时那只眼睛只是玻璃体腔液体稍微浑浊,没有新的出血。由于手术中的处理是得当的,就按计划安排他第二天出院了。
问题就出在了术后第二天。
玻璃体视网膜手术,术后视力并不会像白内障手术一下子表现得很好。第二天病人一揭开纱布,突然发现看不到0.1了,只有数指的视力,在病房里就闹开了。
首先是质疑手术是谁做的。“当时明明是一个老专家,怎么给我做手术是个年轻人”(因为我比接诊的经治医生年轻一点),“那个医生不让做,你就非要给我做手术,而且是个年轻人拿我做实验”,“这个手术把我的钱花了,我也看不到了”,坚持不肯出院。可是,按照床位计划,新的病人已经来了。
我去病房跟他沟通。当时我也有一些情绪。我冒了风险做手术,病人不但不理解,还要责备我,搞不好还要去告我。刚好这个时候他的儿子从外地赶来了,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。
我将他带到办公室,告诉他父亲的病情是什么样的情况,还拿来一张正常眼底图片来和他父亲的眼底图片做对比,让他明白严重程度。
有意思的是,手术前我认为是上台去做一次“赌博“,一方面要留点证据,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一个人来做手术,期望值又这么高,担心将来有纠纷,就做了个手术录像,记录手术中的操作情况。
这个时候我就把手术录像拿出来给他看,并说明这只眼睛回去后还需要观察期和恢复期,视力会慢慢恢复。
这样沟通之后,他的儿子接受了解释,把父亲接回家了。
两个星期后,在儿子陪同下病人来我门诊复查,视力已经提高到0.12(后来还有提高)。这次一见到我,他就问:“我的手术是你做的吗?我还要做另一只眼睛。”
我说,我能把这只眼睛保下来已经是万幸了,你还在病房里跟我吵架,你对我这么大的责备、不理解,医院去告我。
他一下子跪了下来,求我治疗另外一只眼睛。
我说,把你这只眼睛保住,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;另一只眼睛已经失明好几年了,以现在的医疗技术水平是无能为力的,确确实实是没有救治的机会了,咱们就别花这个钱了,因为肯定没有好的结果。
其实,从医生的角度来说,这就是一个关于“担当”的故事。
从刚做完手术时的不理解,到两个星期后跑到诊室来跪下要求我做另外一只眼睛,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。我们一点点的担当,就能够给病人带来光明,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
但是,什么时候能做,什么时候不能做,要视具体情况而定。作为医生,一定要把自身的本领练好。没有足够的能力却要去担当,可能就会造成伤害。
“能感觉到医生是用心在治病,这是一辈子都忘不掉的”
这是今年春节前刚刚做完手术的病人,是一位能力比较强的知识女性。由于种种原因,医院待了半年左右时间。因此,当她来到我的门诊时,对前面的就诊过程有很多抱怨。
起初,她以玻璃体积血就诊。手术清理了积血,但出现了术后并发症,出现再出血。于是医生给她做了一次灌洗,但不久之后又出血了。
这样的情况让病人很不满意,“做了两次手术,花了这么多钱,还是看不见。”而且专家跟病人沟通时间太短了,“一分钟就把病人打发了。”还有,因为手术是麻醉的,而且眼睛是盖住的,看不见手术者,“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专家做的手术。”她对手术失败的原因产生了一系列怀疑。
为了打消她的疑虑,我在门诊特意空出时间跟她做详细的沟通。首先,给她解释手术的难度,并请她放心,一定是专家本人做手术。然后,我仔细翻阅以前的资料,把整个疾病的过程,发生、发展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并发症都仔细解释清楚。
沟通的目的有两个,第一,让患者了解自己的病情;第二,消除以前的一些疑虑。
对于这种疑难复杂的病人,沟通的时候一定要小心,既要让病人满意,又要保护好我们的同行,不让潜在的纠纷风险扩大化。
经过这样的沟通,她提升了对我的信任度,最后决定,“我还想再做手术,还有机会吗?”
跟患者沟通,在提升信任度的同时,往往也提高了患者的期望值。这个时候就需要平衡各种关系。在医学实践过程中,仅仅依靠医学知识或技能治疗疾病是不够的,还要综合考虑人文、心理等因素。
因此,进一步沟通的时候,我就分析了她当前的疾病状态和既往手术情况,讲明再次手术存在的风险,让她做好心理准备,“我们一起来努力,”其实,“医生和你的目标是一致的,都是希望你的疾病得到很好的救治。”
进了手术室,我就让她看到我,还跟她说了几句话。手术过程中也不时地